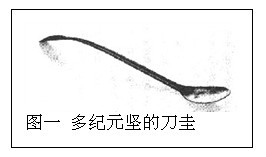|
|
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
×
廖育群
(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,北京 100010)
自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,至1868年明治新政诞生,是史家称之为“近世”或“江户时代”的日本封建社会晚期。在这一时期,由于幕府以朱子学为官学,从而使得儒学脱离此前依附于禅宗的从属地位而独立发展。继而又出现了与其争相斗艳的古学、折衷等儒学流派,兼之当时虽已有以“兰学”为代表的西学存在,但所涉内容尚不及政治、哲学等领域,所以构成了儒学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、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。
另一方面,就技艺之学而言,由于医学自身所具有的种种特点——既是“仁术”与“格物穷理”之一端,又是官吏之外的文化人体面谋生的最佳选择,且与所有人的生活需求都具直接关系,因而尽管医学不如儒学高贵,但也同样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与青睐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当时的“自然科学”,几乎就是医学。而在当时日本的“西学”中,医学也是主体。
同时,“儒”与“医”之间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能够以儒谋生者,视“医”为“学”,故乐于研究;志在行医济世或无奈只能业医者,或因视儒学为基本素养,或为满足“儒志医业”的心理需求,通常也都有投于名儒门下学习的经历。从而构成了儒者与医者、儒学与医学间的密切关联。
自16世纪以来,日本在不断吸收中国医学最新成果并加以改造,逐渐形成同源而异流之汉方医学体系的过程中,先后出现了四个主要的流派。首先是以曲直濑道三(1507-1594)师徒为代表、以宋明医学理论与治疗方法为主体的所谓“後世派”;其后则是独崇汉代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,认为只需根据病症选择药物,全面摒弃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、脉诊等中医基础理论的“古方派”;以及折衷“古方”与“后世”或“汉法”与“兰方”(荷兰医学)的折衷派。在此基础上,最后又出现了注重文献研究的“考证派”。
一般认为上述后三个流派的产生,分别受到儒学复古、折衷与考证之风的影响。本文所要讨论的仅仅是与儒学折衷、考证之学既有密切关系,又非一语即可说清的医学考证派。迄今医史学家对于这一学术流派的论说与评价,或是将其并入“折衷派”而一语带过;或是盛赞其为“高度学问性业绩”,是 “可以在全世界引以为荣的文化遗产。”[ 小曾户洋:“目黑道琢”,第13页。作为“解说”,载于收录考证派医家目黑道琢著作的《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》第107卷(东京:名著出版,1983年)。]或谓因考证之兴,前世“臆造之说胜,而订诂之义微”的“粗梗武断之风始除”[ 浅田宗伯:《皇国名医传·多纪桂山》。见《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》第99卷(东京:名著出版,1983年),第541页。];或在认可这一说法的同时,又感叹“可惜此前因古方家而将勃兴的日本医道,至此再度退到蒙昧之中。”[ 富士川游:《日本医学史》,东京:日新书院,1941年,第438页。]或褒其治学、育人之功;但又斥其把持教育方向、导致“学”与“术”分离之过等等。史家所以会有仁智不同的种种评价,除各自视角、价值取向不同外,还在于产生与活跃于江户时代中后期、构成明治維新取缔汉方医学之前最后一道亮丽风景线的医学考证派,不仅自身的学术构成十分复杂,而且是由诸多有血有肉有情之躯构成的、与社会具有种种联系的一个共同群体。
一、从儒学到医学的考证
利用各种方法,揭示文字记载之历史的本貌,或文字语言所要表达的本义,即是考证。因而对于历时千载之文化积淀的儒学与医学,无论是立足史学解释还是现世应用,都离不开考证。所以在所谓考证学派出现之前,“考证”实际上已然客观存在于儒学的“古学派”与医学的“古方派”之中。但这与继折衷派之后出现的“考证派”,毕竟在目的与价值取向上不可同日而语。
对于形成于江户后期,构成一个医学流派的考证派,石原明是这样描述的:
“考证派之源发于折衷派,是受清代儒学中之新学风影响而形成的学派。……日本亦有以井上金峨、吉田篁墩等为核心的考证学兴起,试图融合古方派与后世派长处之折衷派的一部分人受其影响,通过多纪元惪、目黑道琢二人,形成了以文献学为中心论证古典之整合性的医学中的考证派。狩谷掖斋以‘实事求是’为口号的书志学性研究,通过一手掌握幕府医事行政的多纪氏家族得到扩充,考证派最终压倒其它传统医学各派,成为幕末的医学主流。而且不断有灿烂的巨著面世,表面上似乎体系完备,但作为医学的内容,在临床方面并没有脱离单纯根据经验的折衷派之藩篱,学与术完全分离。至多纪氏三代之元简及其子元胤、元坚的时代,出自目黑道琢之门的伊泽兰轩及享誉‘兰门五哲’的高足——涩江抽斋、森立之、冈西玄亭、清川玄道、山田广业等的共同研究的古医书的书志学性研究,通过后来由森立之编纂成的《经籍访古志》八卷与《留真谱》十卷而流传,作为宋元版与旧钞古医书的研究,堪称空前绝后的文献。”[ 石原明:《日本の医学》第二版,东京:至文堂,1963年,第172页。]
在这段简短炼达的文字中,不仅概述了考证派形成与发展的源流,还给出了儒、医两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与成就,以及他们的地位与学术特征。首先是如何从儒学折衷派中产生出考证派的问题。
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在朱子学、阳明学、古学派相继兴起后,又出现了力图超越各学派的对立抗争,以求融会贯通地阐说“圣人之教”,从而引领18世纪后期学术风潮的折衷学派。其代表人物为生活在江户的片山兼山(1730-1782)和井上金峨(1732-1784)等人。兼山一方面批评朱子学和阳明学都是“阳儒阴佛”,同时又承认他们有“一洗汉唐诸儒鄙陋之见”的功绩;一方面认为古学派能够“窥见先王礼乐之宫墙,其功至大”,但又责备他们“难免自以为是之过。”总之,兼山的主张是提倡到中国秦汉以前的古书中去寻找“古道”。而他所说的古书,既包括儒家,也包括其它诸子百家;甚至佛教思想也并非完全不足取[ 以上有关片山兼山的介绍,均引自王家骅《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》(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1990年),第144页。]。
另一位更具影响,且与江户医家具有直接联系的名儒井上金峨的祖、父均为医家。至金峨辞其禄,改业为儒。从井上兰台学荻生徂徕[ 荻生徂徕(1666-1728),先治朱子学,40岁后因受中国明代学者李攀龙(1514-1570)和王世贞(1526-1590)的影响而脱离朱子学成为古学者,开始在文学方面提倡“古文辞”。50岁后将李、王的文学主张移植到儒学方面,认为古今语言不同,故“以识古文辞、识古言为先”,因而被称为“古文辞学”。在学术上将道德与政治分开,否定了作为“治心”与“修身”的儒学。]之说,后悟其非,遂著书数篇以斥其非,于是名始显。金峨之学,训诂取舍于汉唐注疏,义理折衷宋明之诸家,故谓之折衷学。由是以降,唱其说者接踵而起,江户学风为之一变,徂徕之学渐衰。明和二年(1765)多纪元孝创建私立医学教育机构跻寿馆时,亲将子元惪就其家迎金峨至馆中,一任经营万事,又委托总理学政,于是其名大彰[ 详见森润三郎《多纪氏の事迹》第二版(京都:思文阁出版,1985年),第119-122页。其中录有多纪元惪为井上金峨所撰《墓志铭》的全文。]。
正是由于折衷派不可能离开古书去自由地抒发自己的见解、构建学说体系,因此便成了孕育所谓“考证派”的温床。一些秉承折衷立场的学者(无论是儒者、医家,还是在其它学术领域中),或因个人素养与兴趣所在,或因价值理念更加倾向务实求是,或因受中国清代考证学的影响,在学术上表现出更加注重古典的实证研究,甚至唯考证是务,于是便有了所谓的考证派。井上金峨的弟子吉田篁墩(1745-1798)[ 吉田篁墩:名坦,字资坦;后名汉官,字学生、学儒。通称坦蔵。其家世为水户侯医官,宝历八年(1758)父丧,篁墩袭其医职。后因故夺禄,易名佐佐木坦蔵,至江户为儒。后复吉田之姓。]就是这样一位藏书颇丰,一生“不惜重金购买古书、字画,辨其文字异同,以博洽而闻名”;“专奉汉唐疏传,首倡考证学,近世称宋版、明版等,尊旧椠古钞之事由其而起”[ 森润三郎:《多纪氏の事迹》第二版,第125页。]的学者。富士川游也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考证派从折衷派析出之原因的:“嗣之而起的考证派,倡导折衷,却至其极,遂为训诂笺注之事。”[ 富士川游:《日本医学史》,第370页。]
而前引石原明文中提到的狩谷棭斋(1775-1835)[ 狩谷掖斋:名望之,字卿云,通称三右卫门。少时志于律令之学,穷搜唐典而不得其源,乃上溯汉籍、修“六经”,而恍然有悟。终身尊崇汉学,藏“汉镜”等汉代五物而自称“六汉老人”,问其另外一物为何?答曰:“汉学”。],则是不仅插架亦极富,且因精于鉴别,故被视为书志学嚆矢的人物。可以说,当某些学者的研究重点、价值取向从理论的折衷移至文字与版本的考证后,便派生出只可谓之“考证”,无法再将其统摄于“折衷”之下,近乎独立专门的分支性学科——“校勘学”与“书志学”。这才是“考证”得以自立门户的决定性要素,也就是石原明所说“学”与“术”分离的含义所在——这种研究已然与作为治疗疾病之技艺的“医学”毫无关系。
“考证”之所以得称一派,首先是因为有可资比较的“折衷”存在。而在此之前汉唐疏注,虽然也是考证,但却无学派可言,因为那就是当时的经学。“折衷”与“考证”两个学派,在学理层面上呈现出的图像是:后者源于前者,但又有千丝万缕无法确分的关系。于是才会有或着眼于“同”,而将其并入折衷派;或着眼于“异”,而将其另作一派的不同观点。可以说日本医学史著作,基本上都是站在上述“以儒为本”的立场,或详或略地论说医学考证派的产生与源流。一言以蔽之,即在吉田篁墩、狩谷掖斋两位最主要的儒学考证派人物影响下,医学领域也随之出现了考证派。例如森润三郎据海保渔村[ 海保渔村(1798-1866):名元备,字纯卿,通称章之助。大田锦城之弟子。安政四年(1792)以元坚之荐为医学馆儒学教授。]为森立之等编撰的《经籍访古志》所写序言,将考证学从儒到医的扩展过程,描述为[ 森润三郎:《多纪氏の事迹》第二版,第6页。]:
1、吉田篁墩的“旁系”→多纪元简
2、狩谷掖斋的“直系”(从游、受教)→涩江抽斋、森立之
“旁系”→市野迷庵、多纪元坚、伊泽兰轩、小岛宝素
3、涩江抽斋、森立之2人的“旁系”→多纪元昕、伊泽信道、小岛尚真、堀川济、海保渔村
然而在海保渔村撰写于1856年的序文中,只不过是说:“篁墩同时有若桂山丹波君(多纪元简)”;“卿云(狩谷掖斋)所友则又有若迷庵市野光彦,有若宝素小岛君学古及伊泽兰轩,相与上下其议论,而藏书亦皆颇富”;“而茝庭丹波君亦柔(多纪元坚)亦尝与卿云交最亲” [ 见《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》第53卷(东京:名著出版,1981年),第270页。]云云——不过是同时代或密友而已。
如果注意一下医学考证派代表人物的生年——例如前引石原明文中所言及的多纪元惪、目黑道琢均大大早于吉田篁墩和狩谷掖斋,以及这些医家之间的血缘、师承关系,则会想到实际情况也许未必如此简单。 |
|


 窥视卡
窥视卡 发表于 2009-9-30 11:20:14
发表于 2009-9-30 11:20:14

 提升卡
提升卡 置顶卡
置顶卡 沉默卡
沉默卡